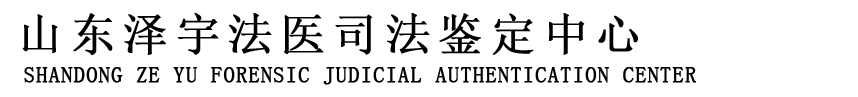

联系电话:0538-8211577
咨询热线:0538-8332366
欢迎访问山东泽宇法医司法鉴定中心网站,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480号中南樾府17号楼10层
摘 要:2016年修改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在体系结构优化和司法鉴定质量强化等方面具有实质性的进步意义。但在“协议书”修改为“委托书”、规定“相关专业”以及诉讼外“参照本办法执行”等方面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对这些问题由于未作出清晰地说明,致使其在实施过程中颇具争议,亟待理论从鉴定本质、鉴定规律以及学界在术语的共识上作出符合法理的解释,以便化解司法鉴定实践中的不统一做法以及法庭上出现的不应有诘问,进而保障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在实施中的有效性与维护其程序的权威性。
The interpret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n some issues of the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Guo Hua
(Law School,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amendment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Judicial Expertise Procedure made real progress in th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judicial expertis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cognitive divergences about modifying the concept agreement to proxy, setting up the concept relevant profession, regulating that these Measures apply by analogy out of litigation. As there is no 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se divergences, we met lots of disput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Judicial Expertise Procedure. It’s hard time for our theorists to make an explanation, which is in line with legal, for the essentials, rules and consistent academic terms of judicial expertise procedure. Only in these way can we solve these differences in practice and undue disputes in court. Then the validity and authoritative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Judicial Expertise Procedure can be maintained.
Key words: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interpretation of some issues; Jurisprudence Consideration
2016年5月1日实施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以下简称《程序通则》)是在2007年《程序通则》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有关司法鉴定的修改尤其是司法改革不断深化对司法鉴定的要求以及在实施过程遇到的新问题进行的修订。这次修订以问题为导向,侧重于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注重于优化司法鉴定程序的结构体系,着力于提升司法鉴定质量,具有一定意义与价值。[1]由于对《程序通则》未能作出诠释,以至于在其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不一致、做法上的不统一与理解上的较大分歧,甚至在个别条款的适用中出现不知所措的情况。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影响了《程序通则》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折损统一司法鉴定管理统一体制改革的效果。本文选择《程序通则》实施过程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解读,并提出管见,以飨大家。
1 司法鉴定协议书与委托书的变化与思考
新修改的《程序通则》将原来司法鉴定机构应当与委托人签订的“司法鉴定协议书”修改“司法鉴定委托书”。这一修改带来以下问题,为何作如此修改?协议书与委托书存在何种本质上的区别?委托书包括哪些基本内容以及是否需要全国统一“委托书”的格式?这些问题在目前不仅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而且实践中也存在一些不同的做法,亟待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较为充分的说明。
新修改的《程序通则》第十一条在委托主体上明确为“办案机关”,而在第四十八条将办案机关又界定为“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从我国职权主义诉讼制度来看,这种规定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尽管刑事诉讼法将需要鉴定采用了“指派、聘请”术语,但在有关刑事诉讼法的适用解释中鲜有采用“委托”术语的情况。一般而言,侦查机关需要鉴定时,多数指派其内设立的鉴定机构实施,并采用指派或者聘请的方式进行。例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 二百三十九条第 二款规定:“需要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批准后,制作鉴定聘请书。”侦查机关需要其以外的鉴定机构(主要是社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时,也多采用“聘请书”方式。这是因为我国将鉴定规定在侦查程序中,并将其作为侦查行为所致。实践中的审判机关多采用“委托书”的方式进行委托,况且社会鉴定机构受理的司法鉴定多为审判机关。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二百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同意重新鉴定的,应当及时委托鉴定”。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多采用“委托书”或者“委托函”的方式委托鉴定。例如,《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 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即使是“当事人协商选择鉴定人,但是决定与委托鉴定仍然是人民法院的工作,因此,双方当事人协商意见一致的,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后向双方当事人宣布并向鉴定出具委托函”。[2]《程序通则》将原来规定的“司法鉴定协议书”修改“司法鉴定委托书”是符合诉讼法的规定的。
由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司法鉴定委托函是“向鉴定人出具”,而《程序通则》规定的是“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统一受理办案机关的司法鉴定委托”,况且在实践中人民法院的技术辅助部门又是通过所谓的“摇号”来确定司法鉴定机构的,以至于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做法不一致的情况。例如,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关于委托司法鉴定工作的规定(试行)》(京高法发[2011]293号)第七条规定:“市高 级法院随机确定鉴定机构后,诉讼服务办公室应于7个工作日内与被确定的鉴定机构办理委托手续。”对此如何操作在认识与理解上产生了一些疑问。
一是办案机关在委托函中委托的是鉴定机构还是鉴定人。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抑或行政诉讼,鉴定人作为诉讼参与人属于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均存在鉴定人回避以及出庭作证等有关规定,而鉴定机构不属于诉讼参与人,在诉讼法中不宜对司法鉴定机构作出规定。基于此,诉讼法规定的委托对象只能是鉴定人,不可能是司法鉴定机构。而在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中,鉴定人依附于鉴定机构,且鉴定人只能在一个鉴定机构中从事鉴定业务,对外由司法鉴定机构统一受理鉴定业务,受理司法鉴定委托属于司法鉴定机构的职责。那么如何处理诉讼法与《程序通则》的不同要求呢?一般来说,对于具有鉴定人资格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办案机关的委托函委托的主体应当为鉴定机构,鉴定机构确定鉴定人应当告知办案机关,为回避制度实施提供空间;对于没有鉴定资格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办案机关的委托函委托的主体应当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宜是有专门知识的人所在的机构或者单位。
二是办案机关出具委托函后是否还需要再签订委托书以及如何签订委托书。正常情况下,办案机关出具委托函(聘任书)或者委托书后,一般不会再专门与鉴定机构签订另行委托书。因为委托函(聘任书)或者委托书中包括《程序通则》第十六条规定的委托书的部分内容。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第 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委托书中明确鉴定事项、鉴定范围和鉴定目的。”基于委托的含义而言,委托函或者委托书一般是由办案机关单方面出具的,而协议书属于双方协商签订的。那么,在鉴定实践中如何执行《程序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呢?就目前而言,对于办案机关出具委托函或者委托书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宜在再另行要求与其签订司法鉴定委托书,但可以将《程序通则》第十六条规定司法鉴定委托书作为司法鉴定机构确认办案机关对移送的鉴定材料、鉴定期限、鉴定费用等问题的确认,可由办案机关的经办人在此委托书上签字确认,从而作为委托人“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以及司法鉴定机构对“鉴定材料的名称、种类、数量、性状、保存状况、收到时间等”(《程序通则》第十二条的规定)核对的证明。这种方式符合司法行政部门将司法鉴定机构受理与委托的作为管理事项的基本要求,也符合鉴定机构受理登记的基本要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司法行政部门对办案机关签订委托书的内容不宜作出强制规定,即使作出这种要求也不易于办案机关接受,毕竟《程序通则》作为部门规章是对鉴定实施管理上的要求,并非是调整办案机关与司法鉴定机构关系的规定。
另外,委托书的盖章是人民法院的院章还是人民法院内设机构的技术辅助部门的内部章均不影响委托书的委托性质。
2 技术标准、技术规范与技术方法的解读与思考
鉴定技术标准是衡量鉴定意见作为证据可靠性和可信性的重要依据,也是防止鉴定人主观性、任意性、片面性的重要标尺,它不仅有利于减少或者消除鉴定上的分歧,而且还为解决鉴定意见纠纷提供了判断参考。新修改的《程序通则》第 二十三条对鉴定人鉴定遵循和采用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技术方法作出了大幅度的删减,删除了“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中的“技术规范”以及“不具备前款规定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可以采用所属司法鉴定机构自行制定的有关技术规范。”初步形成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以及技术方法”的层次性结构体系。如何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以及技术方法进行科学界定则成为需要解读的重要内容。
我国《标准化法》将中国标准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DB)、企业标准(Q/)四级。国家标准在我国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分为强制性国标(GB)和推 荐性国标(GB/T)。就严格意义而言,《程序通则》规定的国家标准主要包括全国刑事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及其各专业的分技术委员会制定并以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的名义发布的标准。就目前鉴定领域而言,也应当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司发通[2013]146号)以及《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等联合规定。但是,从现有的修改情况来看,与“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的立法逻辑相比较,应当不存在国家层面的“技术规范”。
对于“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主要是指司法鉴定主管部门、司法鉴定行业组织或者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3]不包括各省市制定的所谓“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目前,司法部颁布的多为技术规范。在鉴定中采用“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时,这些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一般应经过司法鉴定主管部门确认,从严格意义上讲,还需要报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新修改的《程序通则》第 二十三条将原来规定的“该专业领域对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修改“该专业领域对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所谓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包括该专业领域知名技术组织或者科学书籍、学术期刊公布的方法、仪器设备制造商指 定的方法以及其他机构使用的成熟方法。实际上,它属于未经过有权部门确认的具有行业性质的“行业技术方法”,并非是法律意义上技术方法,不具有强制力。[4]其中的技术方法不同于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在适用上也应当予以区分。
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技术规范、技术方法的采用问题上,当存在国家标准时,不得采用行业标准;在没有国家标准时,才能采用行业标准;在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行业技术规范时,也不得再采用“司法鉴定机构自行制定的有关技术规范”。新修改的《程序通则》删除了司法鉴定机构自行制定的有关技术规范的适用,意味着这种技术规范不再作为司法鉴定的技术规范。在实践中,采用该专业领域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方法必然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对于此应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予以考虑。在实体方面,对何种技术方法可以作为司法鉴定技术方法除了考虑司法鉴定实践的经验外,还需要参考国外确定鉴定技术方法的标准。国外确定技术方法的标准以1993年达伯特诉麦热里杜制药公司(Daubert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案件最为典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推翻第九巡回地区法院根据弗赖伊判例“普遍接受标准”所作的判决时,确立的达伯特判例的“综合观察标准”或达伯特法则(Daubert Rule)。法庭认为,应采用以下四种方法来检验专家证言是否具有可采性:(1)该科学理论是否得到了实验检验(The known can and has been tested)。(2)作为专家证言基础的理论或技术是否已发表且经受同行严格复查的检验(The science has been subjected to peer review and publication)。(3)作为专家证言基础的研究方法或技术的出错概率有多大(The known or potential error rate of the science)。(4)就专家证言基础的技术、方法和理论而言,在某个特定的科学领域中有多少学者能加以认同和接受(The general acceptance of the science in relevant scientific community)。[5]
另一方面,还应当考虑确定技术方法的程序。由谁来作为主体组织认可?认可该技术方法需要遵循何种原则和何种程序?对于不同意见如何处理?我们认为,对于此问题应当由该专业的专业委员会和适当的法律专家作为组成认可鉴定技术方法主体,通过该专业提出该技术方法的主体对于该技术方法予以说明、解释,由该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吸收基础领域的专家与法学专家予以论证,通过质疑程序来获得该技术方法的认可,以保证其技术方法的可靠性。尽管科学问题不宜采取民主的方式解决,但对于鉴定技术方法而言,仍需要一定的复杂程序来保证其作为司法鉴定技术方法的稳健性以及能够在重新鉴定中使用。这些技术方法不仅要科学,更需要可重复性,得到该领域多数专家认可仍不失为较为一种稳妥的方法。但对认可的司法鉴定技术方法应当由国家司法鉴定主管部门予以公布,接受社会的质疑。
3 鉴定人的相关专业与相应资质的理解与思考
新修改的《程序通则》第三十二条规定:“重新鉴定应当委托原司法鉴定机构以外的其他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因特殊原因,委托人也可以委托原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但原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指 定原司法鉴定人以外的其他符合条件的司法鉴定人进行。”“接受重新鉴定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的资质条件应当不低于原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重新鉴定的司法鉴定人中应当至少有一名具有相关专业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在重新鉴定问题上确立了委托其他鉴定机构为原则和委托原鉴定机构为例外的基本原则,同时要求接受委托的重新鉴定机构的资质应当不低于原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修改后的规定与原规定“重新鉴定机构的资质应当高于原司法鉴定机构相比较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原来的规定在鉴定实践存在一些投诉且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2010年我国遴选了“十家国家级鉴定机构”,如何初次鉴定为国家级鉴定机构,按照原来的规定重新鉴定应当委托高于国家级鉴定机构的鉴定机构来进行,但在实践根本不存在高于国家级鉴定机构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而按照现在的规定,初次鉴定如果在国家级鉴定机构进行的鉴定,则可在国家级鉴定机构中进行。但是,在实践中应当注意的是,在十家国家级鉴定机构中并非其所有的鉴定事项均属于国家级资质,如果国际级鉴定机构的鉴定事项不属于国家级资质的,也在可以在不具有国家级的鉴定机构中进行,不宜简单机械地按照司法鉴定机构的外在形式上的资质确定不低于原鉴定机构资质的规定。
在此条规定中,“负责重新鉴定的司法鉴定人中应当至少有一名具有相关专业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中的“相关专业”极易引起分歧性意见。对此条从字面作为相反解释来看,存在需要“具有一名不属于本鉴定专业的高 级技术职称”的司法鉴定人的疑问,即为什么重新鉴定需要找一个不是本专业的司法鉴定人参与鉴定呢?因为“相关”是相对进行重新鉴定需要专业而言,是指与重新鉴定彼此关联或者相互牵扯的专业。显然,这种解释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重新鉴定的高标准要求。因为重新鉴定要求的更专业,鉴定事项也需要在本专门更具有权威性的司法鉴定人,而不是需要一个与本专业相关专业的司法鉴定人,否则,鉴定的专业程度不是更高了,相反因相关专业司法鉴定人的参与,导致其鉴定专业力量被削弱了。对于此条款应当在立法上规定为负责重新鉴定的司法鉴定人中应当至少有一名具有“本专业(与鉴定事项相符的专业)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
新修改的《程序通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司法鉴定人完成鉴定后,司法鉴定机构应当指 定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对鉴定程序和鉴定意见进行复核;对于涉及复杂、疑难、特殊技术问题或者重新鉴定的鉴定事项,可以组织三名以上的专家进行复核。”按照此条规定,司法鉴定意见的复核成为鉴定意见出具的必经程序,复核人应当对鉴定意见书提出复核意见。这种复核是程序意义的复核还是指实质意义上复核,是否不进行复核就会导致鉴定意见的存在瑕疵,因欠缺这一必要程序就会致使鉴定意见受到重大影响,甚至无效。同时,“相应资质的人员”是否必 须是“司法鉴定人”?“相应资质的人员”有无专业要求以及与《程序通则》第三十二条“相关专业高 级技术职称”司法鉴定人存在何种关系?“相应资质的人员”复核时与司法鉴定人意见不一致如何处理以及这种规定是否与司法鉴定人独立鉴定原则存在冲突?这里的“相关资质的人员”因没有司法鉴定人的限制,似乎可以不是司法鉴定人。如果从事此司法鉴定的司法鉴定人员是高 级技术职称的司法鉴定人,在司法鉴定机构中不存在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人,对此问题如何处理必然成为实践中的难题。如果复核人与鉴定人存在不同意见,是以鉴定人的意见作为鉴定意见还是以复核人的意见作为鉴定意见,从鉴定人独立鉴定的原则和出庭作证的要求来看,复核人应当尊重鉴定人的意见,否则会违反上述原则,也会导致鉴定人出庭作证成为困难。基于此,复核人实质上是对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的程序性,不仅对鉴定意见作实质性审查,更不能更改司法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如果复核人发现鉴定意见存在瑕疵或者存在错误,应当建议鉴定人进行检查或者重新作出。鉴定意见由鉴定人本人基于自己的专业判断作出结论,司法鉴定人对鉴定意见负责,独立承担错鉴的责任。一旦鉴定人不接受复核人的意见,在此方面涉及责任分担问题,必然成为司法鉴定人责任追究的凭据。
4“参照本通则规定执行”与诉讼外委托出具鉴定文书性质的诠释与思考
新修改的《程序通则》第四十九条规定:“在诉讼活动之外,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依法开展相关鉴定业务的,参照本通则规定执行。”对此条款规定的“参照本通则规定执行”应当如何理解?对于诉讼活动外委托鉴定出具的鉴定文书是作为鉴定意见抑或作为书证等其他性质的证据材料?上述问题如何理解成为目前必 须面对的问题。
对于参照执行问题,因人们对参照的不同理解会产生分歧。此处的参照是否必 须按照执行,不按照执行存在何种法律后果?规定参照是否意味着有些规定可以不参照,否则何不规定依照或者按照?对上述疑问的理解源于对何者为“参照”的不同解释。我国《现代汉语词典》对“参照”解释为:“参考并仿照(方法、经验等)。”也就是说,当若干件不相同的事物需要比较时,就要借助这些事物中共有的形象概念作参照标准,这一借助的过程课称之为参照。法律规范上的“参照执行”一般是指与法律文件适用对象相近的单位不再制定专门法律文件,而是要求相近单位参考该法律文件并仿照执行。有观点认为,“参照执行”的一般意思,是指按照其原则和精神“执行”,而不是指“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但在具体问题上允许不违背基本精神或者基本原理上的变通执行。一般来说,对于“参照执行”大致有三种理解:一是认为只是“参照”,可以不执行。既然是参照执行,那就是参照着执行,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二是认为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是否执行自行决定,执行不执行都均可;三是认为“参照执行”强调的是执行,并不非是不执行,而是一定要执行。第 一种理解侧重于参照,充分体现参照的意义,但是忽略了执行的意义。第三种理解则侧重于执行,却忽略了参照。有观点认为,从“参照执行”的字面意义来分析,不排出包含了上述前两种含义,但主要或者更多的是体现了第三种理解精神即要求执行,甚至是在条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必 须制行。如果允许不执行,也就失去规定的意义,法律完全可以不作规定或作出相反的规定。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于本条文规定的“参照本通则规定执行”成为了鉴定机构一项义务。因为《程序通则》规定的“参照执行”所表达的意义应该是执行,而不是可执行也可不执行。如果是表达的可执行也可不执行甚至不执行,此条规定的也就有是多次一举的嫌疑。但是,从“参照”字面意义来看,“参”的基本含义是“加入”、“参加”,而“照”是指按照、比照的意思。也就是说,对其规定的基本宗旨仍是要求司法鉴定机构在接受诉讼外鉴定委托时,特别是“实施鉴定”时应纳入《程序通过则》的规范,比照通则的规定一并执行,而绝 不是让鉴定机构在“实施”鉴定时作为“参考”。从鉴定的本质而言,鉴定本身不因委托的主体不同或者诉讼外而与诉讼中有何区别,鉴定程序通则尽管有法律程序正当的蕴含,主要还是遵循了鉴定规律,况且鉴定程序通则是对司法鉴定的最低要求,属于不得突破的程序底线,因此,对此理解为按照或者依照最为恰当。
那么,参照执行对司法鉴定机构实施诉讼外鉴定是否具有约束力。就其约束力来言,参照属于介于遵照和参考之间的术语,根据约束的程度来看,遵照、参照、参考有依次递减的趋势。遵照执行的约束力最强,具有强制的法律约束力,有必 须执行或者应当执行的意蕴;参照执行相对遵照执行约束力较之弱些,但因其具备约束力,还是有一定法律效力的,如果存在不执行或者不宜执行的特殊情况,应当说明理由,即不执行为例外;参考介于两者而之间,几乎没有约束力,可由执行主体自行选择执行与否。我们认为,对于本条规定的“参照执行“,不仅需要参照《程序通则》的精神执行,更为重要的是在鉴定实施过程中应当按照鉴定规定进行,不可随意自由裁量适用。对于委托程序和出具的鉴定书的形式可以作出变通执行,但对于这些非“实施鉴定”的事项不影响鉴定的实质问题。
我们认为,当根据鉴定的实际情况不宜执行或者不执行时,主要集中在委托程序中问题和鉴定书出具程序。对于前者,需要解决问题是,能否不采用委托书而采用原来的协议书?诉讼外委托毕竟不同于诉讼中的委托,尤其是当事人自行的委托,采取这种方式委托的鉴定出具的鉴定书并非是法定的证据种类,即使在诉讼中当事人没有异议,仅仅标明当事人的承认,其法律后果仅仅发生案件事实的承认,对方当事人不再承担举证责任。基于此,司法鉴定机构接受诉讼外鉴定委托,是采用委托书还是协议书的形式,可由司法鉴定机构根据情况选择,防止过分机械而出现片面性,也不宜强行采取统一要求。
一般来说,对执法机关或者查办案件机构以及调解机构、仲裁机构委托的鉴定,应当选择鉴定委托书的方式。因为这些委托行为具有职务行为的性质,与诉讼中办案机关的委托无本质的区别,同时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中,执法过程获取的有些证据可以不经过转化,直接作为诉讼证据。例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十四条第 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经人民检察院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对于当事人自行委托的鉴定,司法鉴定机构可以选择委托书还是协议书,由司法鉴定机构与当事人协商。我们倾向于采用协议书,对有些鉴定事项应当从严,特别是对检材和鉴定目的在协议中应具体化与细化,以免出现鉴定后不必要的争议甚至引发一些因协议不清或者不明的投诉。
对于诉讼外委托的鉴定出具的鉴定文书可以采取变通的方式解决,也可采取与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同的表达形式。对此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采取鉴定书的形式,在鉴定书上盖司法鉴定专用章或者鉴定机构的公章;另一种意见认为,采取鉴定报告的形式,在鉴定报告上盖鉴定专用章。多数意见倾向于采用“鉴定书”,在其前不加“司法”限定,以示与诉讼中的司法鉴定的区别。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第 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就案件事实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出具的专业性意见,适用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关于书证的规定。”此规定也标明办案机关的委托与当事人自行委托出具的鉴定书的不同,适用有关书证的规定说明未将其作为法定证据类型的鉴定意见。这从另外一个层面也反映出无需按照《程序通则》规定执行而可以变通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对于办案机关委托的,应当以“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文书形式。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 二百四十二条规定:“鉴定后,应当出具鉴定意见,并在鉴定意见书上签名。”对于办案机关委托的鉴定采用“司法鉴定意见书”既标明“鉴定意见书”的特性,也体现司法鉴定的法定“司法”的特点。对于当事人自行委托的,可以采用“鉴定书”的形式出现,以示不具有当然的司法鉴定所具有的作为证据的“法定性”,但仍是鉴定,当事人的认可的,也不失为作为证据的意义。
由于参照执行存在人为判断空间,一旦适用不当往往会影响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严肃性,因此,起草规章制度时应可能减少参照执行,必 须将相近类型组织列为参照执行的,应考虑参照执行单位的实际情况,在相关不适宜参照执行单位执行的条款中给予明确注明。当然,制定法律法规规章尤其是规章以及相关实施细则尽量少用“参照执行”的表述,以免在实践中造成分歧甚至给那些善于规避法律法规规章的机会。
新修改的《程序通则》实施过程中的疑难问题不限于以上问题,本文仅仅挑选出自己认为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并将其视为疑难问题作出了一些理论上的思考。既然作为解释与思考则存在不成熟的观点与想法,其解释与思考也仅仅是一孔之见。如果这些问题能够进入讨论的视野,将其作为争议问题也就成为了实质意义上的疑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实现了本论文的目的。
版权所有:山东泽宇法医司法鉴定中心
鲁ICP备19045513号-1
 鲁公网安备
37090202000901号
鲁公网安备
37090202000901号
联系人:梁主任 电话:0538-8211577 0538-8332366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东岳大街480号中南樾府17号楼10层
网站 建设、 百度(360、搜狗)推广、微信营销、400电话办理、泰安网络公司、技术支持:焦点网络(电话:0538-6632526、 8250118) 【管理登陆】